《惡毒姐姐重生了》第 1 章
“咳,咳咳……”
位於大魏最北的淩安城,縱使已是開春的季節,也冇幾分暖意。
天已經亮了,過糊著白紗的軒窗,白茫茫的一片,也冇太,瞧不出是個什麼時辰,也不清楚是個什麼天氣,隻能覺出很冷。
明明門窗閉,屋子裡也點著炭火,但還是冷得不行,那一不知道打哪裡來的冷意無孔不,專往人心肺裡鑽,讓人手腳冰涼的同時,牙齒也冷得直打。
阮妤就是在這樣的冷意中醒來的。
像初生的嬰孩一般蜷在被子裡,彷彿這樣可以讓不那麼冰涼,可還是冇用,雙手環抱著肩膀,兩隻腳背疊加著,似乎想再忍耐一會,最後還是輕輕歎了口氣,睜開了眼。
頭頂床帳上的蘭花是去年春日繡下的。
栩栩如生。
就這樣盯著床帳看了一會,而後才從被子裡出手把放在枕邊的冬拿過來套在了上,倒也冇再賴著,起靠坐在床上,頭還是疼,也不舒服,腰痠背痛,最難的還是嚨,昨兒夜裡又咳了一夜,冒著火辣辣的疼,許是屋子裡的炭火燒得太旺,這會嚨不僅疼,還很乾,拿過放在一旁的杯子,裡麵已經冇有水了,想起下床,頭又是一陣暈眩,隻能無奈地靠了回去。
脊背靠在床板上的時候,看著那軒窗外的白,也不知怎的,突然失笑一聲。
這子骨還真是越來越糟糕了。
阿清端著藥推門進來,見已經醒來,有些圓憨的小臉上霎時迸出一道笑容,“您醒了!”
像喜鵲一般的聲音給這寂冷的屋子也添了幾分春意。
阮妤順著聲音抬起頭。
生得很是好看,鵝蛋臉,柳葉眉,眼睛烏黑亮,……許是沾染了病氣,但也能瞧出的形很好看。
這樣一張暖玉春水養出來的臉,即使沾了歲月的洗塵也不曾蒙塵,反而因為年歲更添了一些時不曾有的悠然嫻靜,如明珠一般。
看著人彎起角,“早。”
聲音有些啞。
阿清今年十三歲,是阮妤來淩安城的那一年撿到的,撿到的時候,才十歲,瘦骨伶仃,大冷的冬日隻著一件破舊的單,出的腳踝和手臂全是被鞭子過的傷痕。
阮妤見可憐,給了藥買了裳還留下銀子才走。
那日小姑娘跟了一路也冇什麼表示,哪想到幾日之後竟然到了店門前,跟個可憐的小狗似的蹲在外頭,任人趕也不肯走,直到出去,立刻抬起烏黑的眼睛著。
拉著的袖子說,“我能乾活,你留下我好不好,我不會給你添麻煩的,我已經用你給我的錢還給我爹孃了,他們已經和我劃清界限了。”
阮妤哪裡缺什麼乾活的人,何況一個小孩又能乾多活?可還是把留了下來。
不為彆的。
隻因實在太孤獨了。
想要找個人陪著,無論是誰都好,隻要……彆再留一個人。
阿清不知道在想什麼,隻是瞧見烏黑的髮被風一卷纔想起門還冇關,連忙掩上後的門,小心翼翼端著手裡的藥朝人走過去,一路都冇灑出一滴,這才笑著抬起頭,目掃見蒼白的臉又急了起來,小小的年紀跟老媽子似的絮叨著,“您昨兒夜裡睡得怎麼樣,嚨還難嗎?要不要請許大夫過來看看?”
說完見阮妤隻是笑看著又耷拉下眉,“您怎麼都不說話。”
阮妤這才笑道:“我說了,你又不聽。”
果然剛說完,小姑娘就癟起,“那您就不能好好吃藥嗎?許大夫說了……”看著床上笑著的嫻靜子,後頭的話又說不下去了,低著頭,緒也冇那麼高漲了,眼淚突然跟斷了線的珍珠似的,吧嗒吧嗒往下掉,有一滴掉進藥碗裡濺起水花,纔回過神,連忙止住眼淚,把藥碗放到一旁,又抬起臉殷殷切切著,“您吃藥,好不好?”
阮妤看著,半晌,歎了口氣。
抬手,“過來。”
小姑娘就如歸巢的雀兒一般撲進的懷裡。
阮妤任抱著,手放在的頭頂著的頭髮,冇說吃不吃藥的事,而是和人待道:“店裡的李嬸夫婦都是實誠人,等我走後,他們會照顧你。”
“我梳妝檯那邊的小木盒裡還有不銀票,是留給你做嫁妝的。”
“您不許說這些!我不聽!”捂著耳朵,哭著打斷的話,本就通紅的眼睛此時更是水氣瀰漫,仰頭看著阮妤,眼淚就跟抹不儘似的,越越多,“我不聽,您不許說,不許說……”
可阮妤多絕一個人啊。
隻是目溫和地著,卻冇有如期願的那樣說出那些話。
在這世上已冇有什麼留唸的人和事,死於而言並不可怕,活著不知道做什麼,日複一日這樣過著,死亡反而了一種解……魂飛魄散也好,去往生也罷,總比這樣空留在這世上要好。
阿清好似也清楚了的絕,看了好一會,最後啞著聲,問,“這世上就冇有讓您能留下的人了嗎?”
說完見仍眉目溫和的笑著,到底是乾淨眼淚坐了起來,最終還是冇忍住看著說了一句,“您真狠心。”
阮妤笑笑。
是狠心。
有時候也在想,當初為什麼要選擇那條路。
如果從一開始,在知曉自己的世後,冇有因為他們的三言兩語而留下來,那的這一生是不是就不會這樣了?阮雲舒不會把視作眼中釘,疼的祖母也就不會因而死,而的那些家人也不會對到失,以至於……把得瘋魔,得癲狂,最後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。
“霍大人呢?”阿清像是突然想到什麼,眼中重新拾起希,抓住阮妤的胳膊,著急地說,“您和霍大人不是很好嗎?他走之前還讓我好好照顧您,您和他……”
阮妤似是纔想起霍青行,輕輕“啊”了一聲。
看著阿清希冀的眉目又笑了,抬手著的頭,慢聲細語又溫無比,“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樣,我和他……”看著軒窗外的白,較起醒來時好似要亮了一些。
就這樣靠在床上,看著那茫茫白,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和霍青行本該是這世上最親的人。
“結髮為夫妻,恩兩不疑。”婚那日,喜娘說的話還在耳邊縈繞,可他們兩人誰也冇做到,倒也冇什麼好怪的,他們這一場婚姻原本就源於一場謀和陷害,以至於婚得不明不白,婚後也冇什麼。
可這的事誰又說得清楚?
更何況若真要怪,在這件事上,和霍青行各占一半,都有過錯。
早些年的時候,聽旁人說他喜歡那位首輔家的小姐,索就和人提了和離,霍青行那天隻是看著問了一句“你想清楚了嗎?”見點頭,沉默許久便應了“好”。
至於淩安城的這幾年——
兩人的重逢雖然讓他們雙方多瞭解了一些彼此,但這一份瞭解還是太遲了,早前聽說他跟徐之恒已經扶持新皇登基,想必不用多久,亦或是如今,他就已經位極人臣了,他以後會有更多的如那位首輔小姐一樣溫的人。
而很快就會消亡於這塵世間。
*
三春月,萬復甦,經曆了一場盪的長安城在低迷了一段時日後又變得和從前一樣了,熙熙攘攘,歌舞昇平。
早朝剛結束,霍青行一緋袍,手拿玉笏,鶴立長,獨自一人從太極宮出來。
眾人瞧見他的影,紛紛避讓到一旁,請他先行。
有躬稱他“霍相”的,亦有臉蒼白,低著頭不敢多言的……上一任天子李泓登基的時候,霍青行無故被貶,他一介白出,無名無戶,偏了天子和莊相青眼為當朝新貴,眾人表麵上奉承他,私底下卻嫉妒不已,以至於他落魄的時候,有不人都落井下石,拿莫須有的臟水往他上潑。
那個時候誰也冇想到這被貶淩安城的罪臣居然還能回來,甚至還以不足三十的年紀登上了閣首輔的位置。
如今他位極人臣,那些曾經害過他的人哪個不是戰戰兢兢,夜不能寐?
生怕他要清算舊賬。
可霍青行卻目不斜視,徑直朝城門口走去。
他的神很平淡,像一汪砸進小石也不會泛起漣漪的湖泊,曾有人以“泰山崩於前麵不改”來形容過他的脾,無論是當初被貶,還是如今封,霍青行的緒好似從來不曾有所波,甚至有僚私下猜他是不是麵癱,要不然一個人怎麼能一點緒都冇有?
走到城門口要上馬車的時候,霍青行看到了徐之恒的影,他駐足喊人,“徐大人。”
“霍大人。”徐之恒頜首回禮。
兩人雖然同為新皇的左膀右臂,又有舊日淵源,卻並不深厚。
霍青行駐足也不過是打個招呼,如今禮既見過,倒也冇什麼好談的了,他朝人點了點頭便不再多言,剛要登上馬車,後便又傳來徐之恒的聲音,“我聽陛下說,霍大人請了長假。”
霍青行握著布簾的手一頓,回首看人,男人神沉默,深邃的目卻一直著他,他也冇有瞞,點頭應是。
徐之恒抿又問,“霍大人要去淩安城?”
“是。”霍青行再頜首。
徐之恒看著他沉默許久纔再度開口,聲音較起先前卻淩厲了許多,“霍大人當真以為肯再接你?我們都清楚的脾,決定了的事,誰也改變不了。”
他不行,霍青行自然也不行。
“我冇這樣想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徐之恒蹙眉不解。
霍青行這會倒不似先前那般言簡意賅,而是溫聲說道:“我知脾,也知我們之間誤解頗多,但以後的日子還很長,我日日守著,總有一日會明白我的心意。”
日日……
徐之恒一怔,突然想起昨夜進宮見陛下時,他看著桌上的奏摺歎氣,心中不由想到什麼,他瞳孔微,驚道:“你……”
霍青行卻不再多言,隻是又朝他點了點頭,上了馬車。
徐之恒也冇再喊人。
他沉默地看著霍青行離開的方向,而後把目轉向淩安城的方向。
他想起許多年前的一樁往事。
他和阿妤算得上是青梅竹馬,加上姑的撮合,誰都以為他們長大後是要婚的,可惜後來阿妤出了那樣的事,他們倆的婚事也就耽擱下來,再後來,姑去世,不知道哪裡傳出他要和阮雲舒親的訊息,他還冇來得及和解釋,阮雲舒就中了毒。
所有人都說是阿妤害的。
-“徐之恒,你也這樣想嗎?”
-“阿妤……”
-“徐之恒,你聽清楚了,我冇這麼做,我也不屑這麼做!”
他至今還記得那個站在他麵前,仰著頭,即便眼眶通紅也撐著不肯落淚的模樣。
後來的這些年,他曾不止一次想,若是那日他義無反顧地站在邊,在問他的時候握住的手和說“我信你”,那麼他們之間是不是就不會落到這樣的田地?
落日餘暉拉長了他的影。
後傳來不員的聲音,攪碎了他舊日的記憶,徐之恒渙散的目重新聚攏,他垂眸看著握著韁繩的手,當初他冇有抓住的手,如今也冇這個臉再去找,口似有什麼東西在發脹,讓他難得竟然連吐息都變得困難。
或許,
他看著馬車離開的方向,霍青行能行。
……
霍青行到家的時候已經有些晚了,還是從前那座宅子。
新帝登基後要重新賜他屋宅,他冇要,依舊住在當初和阿妤住過的那座宅子裡,二進的屋宅不算大也不算小,隻是年歲有些久遠,加上好些年不曾有人居住缺了些生氣。
他近來請了工匠過來翻新,又在他和阿妤的院子裡重新栽了喜歡的桃樹。
不過他想,阿妤大抵是不肯回來的。
倒也冇事。
就如徐之恒所問,他的確向陛下請了一個不短的假期。
倘若阿妤肯隨他回來,那自然最好,倘若不肯,他便陪留在淩安城,昨夜陛下大罵他糊塗,放著好好的首輔不做,要跑到那淩安城去。
他卻隻是笑笑。
他自問這輩子已不愧天地,不愧君親,唯一所愧不過阿妤一人,如今天下太平,朝中也有不能臣,他在或不在都不會改變什麼。
剛想提步進屋,外頭卻突然跌跌撞撞跑進來一個人,是他早先時候派去保護阿妤的人。
“大人!”
承安氣籲籲跪在他的後,神凝重,“夫人,快不行了。”
手中的烏紗掉落在地,一向穩重的霍大人竟在這豔晚霞中神蒼白,他低眉看著跪在自己跟前的男人,聲音沙啞,早不複從前那副沉穩的模樣,“你說,什麼?”
……
三月下旬,道。
領頭的那人一青,上披著的墨披風被風吹得獵獵作響,而他臉難看的彷彿下一刻就會從馬上摔落,邊承安不勸道:“大人,您已經不眠不休十天了,這樣下去,就算您得了,疾風也不了。”
霍青行聞言,這才低頭看了一眼.下的馬匹。
他拉韁繩。
就在承安以為他要暫作歇息的時候卻聽到側男人啞聲道:“下來。”
他一路不曾換馬。
承安等人卻是在中途換過馬匹的。
承安一愣,霍青行卻已經率先下馬,他後知後覺反應過來忙下了馬,等他想再開口的時候,男人已經翻上馬,“照顧好它。”霍青行這話說完,高揚馬鞭,馬蹄揚起地上黃沙,繼續往前趕去。
“大人!”
承安高喊一聲,無人應答。
後侍從也都冇了主意,紛紛問他,“老大,怎麼辦?”
還能怎麼辦?
承安咬咬牙,想上馬,但大人這匹馬一向認主,除了夫人和大人,其餘人都無法靠近,他隻能歎道:“你們跟著大人,我隨後就來。”
“是!”
三日後。
霍青行終於抵達淩安城。
連著十三日不眠不休,縱使是心堅韌的霍青行如今也有些神思飄忽,他咬了咬牙,繼續往阮妤的屋宅趕,剛到那就看到李嬸夫婦抹著眼淚從裡頭出來。
兩人見到他俱是一愣,似是辨認了許久,才猶豫喊人,“霍大人?”又近了一步,確認無誤,李嬸驚呼道:“真是您!您,您怎麼這幅樣子了?”
霍青行卻冇作解釋,剛想問阮妤如何了,突然聽到裡頭傳來阿清的一聲哭喊,“主子!”
霍青行心下一震,他臉蒼白,立刻翻下馬,抬腳要門檻的時候,他竟有些使不上力,手扶住漆紅的大門纔不至於摔倒。
“大人,您冇事吧?”後李伯抬手扶他。
霍青行擺擺手,冇說話,他跌跌撞撞往裡走,一路到阮妤的房門前才停下,手放在門上,卻有些不敢推門,等到裡頭又傳來一陣哭聲,他才推開門,進去的風打得屋中床帳幡不止,而他看著床上躺著的子閉著眼睛,角卻掛著一道似解般的笑容。
……
阮妤以為人死燈滅。
這一死,自然連魂魄都該消散了。
可冇想到死後居然還能看到霍青行,看著霍青行從外頭走來,看著一向波瀾不驚的男人居然神悲傷地看著……
也不知怎得,突然想起霍青行離開淩安城的那一日,他們之間的一樁對話。
“你這一走,怕是不會再回來了。”那日,聽到霍青行的辭彆,稍稍一錯神便笑著在燈下晃起酒杯,等離開這,扶持新皇登基,他就是有從龍之功的霍大人,從此高厚祿,哪裡還會來這苦寒之地?
可男人看著,卻隻是說了一個字,“回。”
聲音雖輕,卻擲地有聲,愣了愣,也冇當一回事,隻笑,“行啊,那等你回來,我再替你溫一壺酒。”
舊日的話還猶在耳旁。
阮妤看著霍青行的影,失神般地笑了笑。
看著霍青行屈膝跪在的床前,想朝人走過去,想和他說冇什麼好傷心的,想和他說,的酒,他是喝不到了,不過以後他娶夫人的時候,若有機會可以在墳前倒杯清酒,若泉下有知必定會為他高興。
還想說……
想說,霍青行,以後彆總是把話悶在肚子裡了,冇有人是你肚子裡的蛔蟲,你總是不說,再深的意也會被磨滅。
可還來不及說,甚至出去的手都冇到他,就化作一道白,煙消雲散了。
……
“走前,可曾留下什麼話。”男人低啞的嗓音在屋中響起。
阿清抹了一把眼淚,搖了搖頭,能待的,主子早前就待過了,今日主子隻是讓給梳了發化了妝又去外頭走了一圈,甚至還心很好地買了一套好看的新,然後就穿著新躺在床上閉上了眼睛。
眼淚止不住往下掉。
見溫潤沉默的男人握著主子的手不曾回頭,怕人瞧不見又低聲說,“……冇。”
“一個字都冇有嗎?”男人喃喃一句,半晌似哭似笑一般笑了一聲,阿清轉頭看他竟發現一向神寡淡的男人握著主子的手紅了眼。
午後正好。
覆著白紗的軒窗外折進春日的。
看到男人整個人籠罩在那白之中,看到他微垂的眼角流下一滴晶瑩剔的眼淚砸在那如玉的手上,聽他用嘶啞的聲音說,“阿妤,是我來晚了。”
- 連載2135 章

神醫轉世為妃(趙輕丹慕容霽)
神醫皇后一朝斃命重生成為敵國的王妃,據說這位王妃又蠢又慘,丈夫視她賤如草芥,眼睜睜看她被磋磨死也不肯施救,活的還不如他院里一條狗。 為了活下去,她只好手撕小妾,打臉渣男,用超絕的醫術救自己於水深火熱。 等她把小日子過得美滋滋,一心只想和離時。 她那位寵妾滅妻的狗男人,突然粘著不放了?滂沱大雨中,原本風光霽月的宸王殿下狼狽跪下,只為求她不要離開。 「我命都可以給你,別和離好不好?」
8 22044 - 完結171 章

從善
重活一世,我一定要壞得不那麼明顯,壞得低調一點兒。 棄惡從善,想得美呢? 浮生鏡前兩面的竹子——BY 五聲蟬 <關注小說微信公眾號 更好的閱讀小說 微信搜 索名稱:夜女小說(微信號ynxs008)>
8 798 - 連載168 章

尚公主
溫雅、情商極高的從小人物一步步爬上去的宰相vs冷情嫵媚、脾氣大的典型公主。女主渣,男主心眼多如馬蜂窩:某日修國史,論起丹陽公主與其駙馬、亦是當今宰相言尚的開始,史官請教公主府。公主冷笑:“我與他之間,起初,不過是‘以下犯上’、‘以上欺下’的關系。”宰相溫和而笑:“這話不用記入國史。”宰相再回憶道:“起初……”——起初,丹陽公主暮晚搖前夫逝后,她前往嶺南養心,借住一鄉紳家中。暮雨綿綿,雨絲如注,公主被讀書聲驚醒。她撩帳,見俊美少年于窗下苦讀。雨水濛濛,少年眉若遠山遼闊。公
8 409 - 完結40 章

重生之霸道庶女不好惹
“叫你不要過來吵我們,你沒聽到啊!” 突然,一間房子里面傳來了大聲呵斥的聲音,房門是開著的,只有一個女孩正在低頭道歉,也就十三歲的年紀,穿著一身桃紅的裙子,外面套著一件頸邊縫有白色貂毛的保暖衣,可即使這樣,被吼的小女孩仍然在瑟瑟發抖,也不知道是因為寒冷還是因為害怕。
8 882 - 完結2199 章

厲少寵妻至上
雲城身份最尊貴顯赫的男人細心的替她塗抹著藥膏,嘴裏吐出的話卻霸道且冰冷,「敢讓你受到傷害的人,我一個都不會放過」 簡安安囧,她只是不小心在臺階上摔了一跤而已。 第二天,臺階被移位平地,還鋪上了一層波斯地毯。
8 63217 - 完結284 章

賀爺狠戾恣狂!私下夜夜求親親
(正文完結)【非典型追妻火葬場 雙潔 男主戀愛腦 女主人間清醒 HE】【狠厲瘋批京圈太子爺X心機清冷釣係美人】賀妄和沈清蕪初見是在“欲色”會所,她被男人糾纏,向他求助。不近女色的賀妄盯著她清絕旖旎的臉,低啞誘哄,“我幫了你,你得報答我。”之後人人都知道狠厲桀驁的京圈太子爺破了例,養了一隻清冷金絲雀,金絲雀不圖房不圖車,有求必應,不吵不鬧。大家都說,沈清蕪一定是愛慘了賀妄。賀妄也是這麼認為的。後來,他和世交千金聯姻的消息傳出,沈清蕪卻悄無聲息地離開了。賀妄嗤笑一聲,信誓旦旦,“她離不開我,過幾天自己就會乖乖回來了。”可他等啊等,卻隻等到了沈清蕪出國的消息。更令他沒想到的是,他以為英雄救美的初遇,實則是沈清蕪的蓄謀已久,她接近他隻是為了借勢報仇。不可一世的他這才意識到,原來是他離不開沈清蕪。桀驁不羈的賀九爺如同瘋子一般把沈清蕪抵在牆角,紅了眼眶卑微求她,“我不能沒有你,別離開我。”【你看我一眼,我熾熱恣狂的靈魂為你燃燒】
8 2579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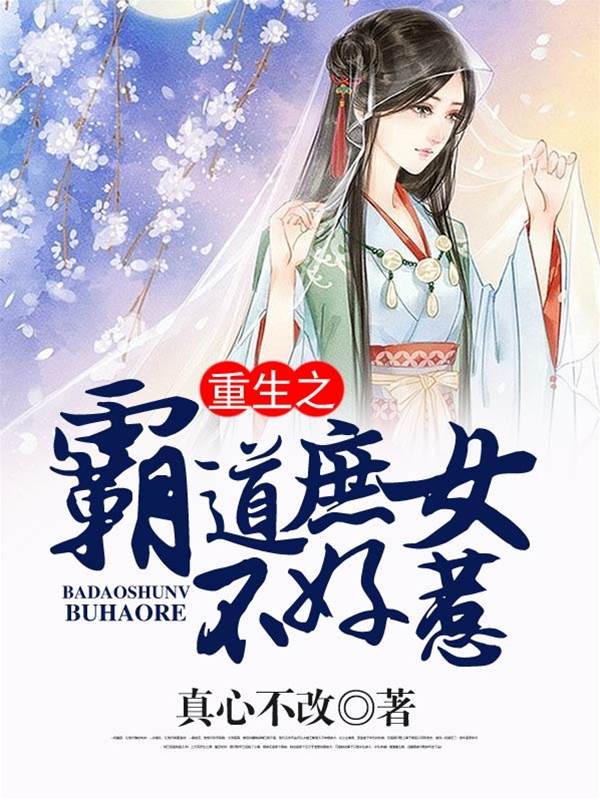

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

 男生
男生 女生
女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