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深眼》第80章 番外終(兩個番外)
番外(7)山水昭昭
年底, 李凌白和全思云的案子正式開庭審判。那會兒李靳嶼和葉濛回了寧綏,李長津跟李卓峰在英國, 庭審出席的只有李凌白的大哥,李維。他全程跟李凌白沒有流, 眼神也沒有, 一不坐了兩小時, 聽法宣讀完判決書,直接站起來,合了合西裝扣子, 一言不發地往外走。
“被告人全思云, 因犯詐騙罪, 判有期徒刑十年, 剝奪政治權利四年;因犯故意殺人罪(教唆引導人自殺定罪為故意殺人罪),判死刑, 并剝奪政治權利終。被告人李凌白, 因犯走私文罪,判有期徒刑八年,剝奪政治權利兩年;犯洗錢罪, 判有期徒刑十五年,剝奪政治權利八年;因犯詐騙罪,判有期徒刑十年,剝奪政治權利四年;犯故意殺人罪,判死刑,并剝奪政治權利終……以上, 如不服本院判決,被告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五日,通過本院或像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訴訟……”
兩人都沒有上訴。
這一場庭審人很多,但格外安靜。分析完案,所有旁聽者陷沉默,震驚于全思云的變態和惡意,和李凌白被洗腦的驚悚。心理醫生這個職業在那年著實被狠狠地黑了一把。旁聽席里有很多悉的面孔,溫延,梁運安,魯明伯,還有那個梁平的,魯明伯的學生。
溫延其實一直以來都不太喜歡魯明伯全思云這對夫婦。魯明伯這人最善道德綁架,李靳嶼那時因為抑郁癥,或許吃他這套,溫延是從來不吃的。什麼最得意又難以啟齒的學生,就是故意說些難聽話,惡心人罷了,因為李靳嶼當時退賽怕影響了他自己的帶隊的績,上明著說不介意,話里話外給李靳嶼施,道德綁架。這些事,溫延是后來聽梁運安和葉濛說起的。
聽完判決,魯明伯的臉慘白。上廁所洗手的時候,見溫延。
“魯老師。“溫延主招呼。
魯明伯瞥他一眼,沒什麼心同他敘舊,嗯了聲,便匆匆要離開。溫延笑了下,整個人靠在洗手池上,不疾不徐地開口,“您跟全老師沒有孩子麼?”
魯明伯聽全思云說過,溫延這個學生最難馴,他可不像李靳嶼那樣自我封閉,客氣、顧及師生分,他不顧的,而且這個學生說話最直白且難聽。魯明伯顯然是不太耐煩,不想同他流下去,轉便要走,溫延又開口住他,“哎,當初全老師是怎麼說服您不要孩子的啊?現在這況,怕也是有些為難了,當然,您這麼德高重,自然多的是小姑娘愿意前赴后繼了,但就是您現在如果再要孩子的話,恐怕……”
他不說了。話頭留了個余味。
魯明伯都走到廁所門口了,突然停下來,面鐵青地回過頭,瞧著溫延:“你什麼意思?”
梁運安站在廁所門口等溫延,聽到聲音也下意識瞧里頭看了眼,隨即無語地翻了個白眼,得,這哥又給人添堵去了。怕是想給李靳嶼報個仇?
溫延直起來,走到魯明伯面前,那張乖張的臉,笑得人畜無害,甚至還手替他拍了拍肩上的灰,“魯老師不要張,我只是出于好意給您個溫馨提醒,全老師也不是什麼都沒留給你的,說不定還給您留了個兒子呢。”
“不可能!早就——”
魯明伯幾乎是下意識大吼。
但很快,便沒了聲。表變得晦不明。往日那些點點滴滴,猜忌漸漸浮上心頭。溫延是心理學專業的高材生,太知道怎麼拿人的痛了。比如全思云真有個兒子,不可能瞞得魯明伯滴水不,兩人這麼多年,必定有過猜忌和爭吵,有些東西,旁敲側擊比單刀直更讓人難。
魯明伯很快陷了回憶的壑里,畫面在他腦海中飛速地切換著——
十幾年前,包里的小孩玩。那些神的電話,他其實好幾次都懷疑全思云是不是在外面找男人了。全思云都矢口否認,魯明伯一直以為是自己多想了。
結果,溫延這話,給了他當頭一擊,不是男人,或許是早年跟別人生的孩子。魯明伯是二婚,全思云沒結過婚,但他知道之前有過一個很相的男朋友。
溫延嘆了口氣,“全老師那麼保守一個人,悄悄跟前男友生下的孩子,這事兒確實也難以啟齒的。”
魯明伯渾一震,臉極其難看。
難以啟齒,難以啟齒,他曾對他的那位學生說過。
“你跟他什麼關系?”
“大概就是如果他愿意我一聲哥,我現在對你說的話會更難聽一點。”
-
執行死刑的前一天,李凌白躺在監獄冷冰冰的板床上,跟獄警要了支煙,然后閉上眼睛,開始慢慢地回顧一生,但發現,已經想不起很多細節了。
比如李明軒是怎麼上的。跟李明軒第一次發生關系是在什麼時候,是誰主的,半推半就,還是李明軒霸王上弓,都已經記不清了。
那天,李長津來探監,文件里是一份親子鑒定,和準確的出生日期。
“凌白,確實我該跟你道歉的。如果當初不是我為了給明軒留個孩子,也不會有現在這些事。”
“你媽媽跟我妻子從小一起長大,兩人關系甚至有時候連我這個丈夫都會嫉妒,后來你媽媽因為一個男人神上出了問題,不顧我妻子的阻攔,生下了你,但很快就病逝了。于是我妻子決定把你收養過來,這個決定是做的,我當時勸阻過,因為□□是一件很麻煩的事,你又是個孩子,我們當時只有一個維程,不太會照顧孩子。”
“那個男人呢?”當時李凌白就著他的話問。
“他得了艾滋病,我找到他的時候,剛拿到檢查報告,他說是你媽媽傳染給他的。他說他從來沒有找過那麼不干凈的,因為他跟小姐都會注意措施,只有跟你媽媽忘記了。你媽媽沒有艾滋病,人也很好,只是因為了一個不該的人。我想,我妻子應該不會愿意把你給他,于是我答應把你收養下來。”
“所以我跟李明軒不是親兄妹是嗎?”
李長津說:“盡管不是親兄妹,但我妻子一直拿你們當親兄妹養,當然無法接你們□□,所以當時我們沒有選擇告訴你們真相,是希你們的能就此冷卻下來,于是我們把明軒送出了國外。”
兄妹三人,李維,李明軒,還有。李凌白清晰地記得,其實跟大哥的關系不冷不淡,李維對好像沒什麼,相比后來出生的李明軒,特別粘,于是大哥就被獨立在外了,他倆關系越來越親。連后來過了界,李凌白都沒能及時收住,而是半推半就地仍由事態發展下去。
因為李明軒英俊帥氣,很粘人,在學校特別招生喜歡,記憶力特別好,智商也超群,參加什麼比賽只要有他基本都是一等獎,眼睛里泛著不可一世的。
李凌白一開始是虛榮,有這麼個英俊迷人又聽話的弟弟,理所當然地寵著他。
第一次越軌是好奇,是試探的。兩人躺在床上,李明軒把手進的服里,委屈地說想看看孩子的,李凌白自然是拒絕的,沒那麼大膽子,當發現事態往著一發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時,開始刻意避開李明軒所有的曖昧舉,但李明軒對越來越過分。那晚,洗完澡,在看經濟學理論,李明軒直接沖進來連服都沒,甚至不給一點反應的時間就強迫著發生了關系。
因為他吃醋了。李凌白那時候已經跟李思楊的父親開始往了。
從那次開始,李凌白發現李明軒的占有、控制都是變態的強,但凡跟男朋友見過一次面,當天晚上李明軒就會睡在房間里,甚至跟說,如果你不愿意分手,我們就永遠保持這種關系。
李凌白非常清楚自己不李明軒,對李明軒的曖昧源于一開始的刺激、虛榮、新鮮,到后來越來越厭煩,恐懼,真真是惡心這段關系。
后來,被李明軒監控的沒有辦法,只能想辦法,故意將這段關系暴在父母面前。
果不其然,他們的媽媽當場嚇暈了過去,李長津倒是顯得格外淡定。兩天之外,他們決定送李明軒出國,試圖讓他們這段關系冷卻下來。
李明軒回國那年,李凌白結婚。那之后其實安逸了很長一段日子,李凌白以為他長大了,然而并沒有。四五年的隔離,反而讓他更加瘋狂。
李凌白生下李思楊那年。
李明軒綁架了李凌白,將囚在自己的公寓里三天三夜,日日夜夜同發生關系。李凌白丈夫報了警,第三日,他們在公寓找到被束住、上遍鱗傷的李凌白,還有因服食過量毒/品死亡的李明軒。
李凌白以為噩夢結束了,但沒想到,懷孕了。理所當然是要打掉的,更沒想到,李長津竟然愿意用份讓把孩子生下來。
現在明白了,那是李長津最的小兒子——李明軒唯一的孩子。
原來才是李家最見不得人的那個。
執行死刑前,李凌白見的最后一個人是鈄花,通過監獄里的3qc視訊。老太太跟穿了同系的服,上嘖嘖,扯了扯擺說:“哎喲,撞衫了。”
一句輕飄飄的話,卻讓李凌白失聲痛哭。
“真丑,你穿這服真丑。”鈄花喃喃說,自顧自地對著視頻碎碎念。
十天后,李凌白和全思云被執行死刑。
十二月,過去的恩怨如同那些霜雪漸漸融化在循環往復的日子里。那年冬天格外漫長,風雪來了又走,禿禿的黑枝椏總也不出新鮮的芽,荒草遲遲不生,依稀似乎還能聽見春蟬夾在的泥層里,呀呀地喚著,春天什麼時候來呀。
“春天馬上就來了。”樹說。
“今年冬天死了好多蟬呢。”蟬說。
“一樣,地球上也死了很多人,”風說,“但也有很多人重獲新生,不說了,小蟬蟬,你好好練練嗓子,等春天來了,你要唱響嘹亮的開幕曲。”
“你趕著去哪啊?”蟬問。
風說:“去告訴海浪,對人們溫一點。”
番外(8)與你昏昏
草長鶯飛,萬溫。
過年那幾天,李靳嶼有點冒,吃藥也不見好。那陣病毒流肆,各公司單位復工時間都延遲了一周。李靳嶼主要是怕傳染給老太太們,便準備回三水塔那邊的房子單獨隔離幾天,大年三十再回來。
別墅熱鬧,老老小小們在進行各種平常不怎麼玩的娛樂活。
老太太們和大姑二姑正激四地著麻將,沒聽他說什麼。
鈄花坐在椅上,膝蓋上鋪著毯子,鼻梁上駕著一副老花眼鏡,神格外專注地盯著徐瀾的牌:“哦。”
徐瀾手上著牌,眼睛盯著牌桌上,以為他只是說出去買個菜,隨口應道:“好的,寶貝,我要吃茼蒿,晚上可以煮火鍋。五萬。”
大姑二姑隨之應和道:“我倆要花菜。”
徐瀾:“花菜就是茼蒿。白癡。三萬。”
大姑反駁:“不一樣好吧,茼蒿是長得,花菜是短的。”然后慢悠悠丟出一張四萬,明顯是算到了瀾士手里卡四萬。然后只見瀾士氣定神閑地把兩個打出去的三萬和五萬撿到一起,“吃。”
鈄花默默拿出小本本記。
原來打出去了還能吃。
大姑:“……”
二姑:“……”
老爺子:“快點打!我要看櫻桃小丸子了。”
“……”
李靳嶼忍不住提醒:“,您數下牌,這麼打,可能會一張牌。”
徐瀾一臉淡定:“等會再這麼吃兩回,就不了。我心里有數。”
“……”
葉濛那幾天正在忙年后的泰國游,訂機票,訂酒店,做攻略,忙得焦頭爛額,所以當時也沒說什麼,趴在床上豎著腳,一邊用ipad做筆記攻略,一邊頭也不回地對他說:“那你到那邊好好照顧自己啊,寶貝。”
李靳嶼當時靠在門上,后是悉悉索索的麻將聲。
他走過去,把床上那人反過來,兩手撐著兩邊,葉濛正寫到盡興,連連哎了兩聲,“等下等下,我還沒寫完呢,普吉島好幾個沙灘,我看看哪個最干凈,風景最。”
李靳嶼居高臨下深深地看了一會兒,然后低下頭,在耳邊低聲說:“你要是想跟我在海里做,我可以告訴你哪個海灘最干凈。”
葉濛一下就老實了。臉熱,被他圈在床上,玩著他前的拉鏈,有一下沒一下地拉著,心頭有燎原的火,忍不住仰頭去親他,被他撇開頭就避過,有種得逞的懶洋洋:“冒啊姐姐。”
葉濛推他,嘟囔:“那你勾我干嘛。”
“這就勾了?”李靳嶼撐在床上,笑得不行,“那你也太不起勾了。”
那幾天。窗外還是偶爾有鞭炮聲,小鎮很安靜,偶爾的鞭炮聲倒添了幾分煙火氣。
大年三十,李靳嶼回別墅。
李靳嶼進門的時候,鈄花正在教葉濛怎麼包餃子。
鈄花一手掌著餃子皮,一手輕輕地在掌心上打著圈:“對,就是這樣,住,要有褶子,不要直接,了!哎呀,你個小笨蛋。”
一盤狼藉,拉拉雜雜,破損千萬。
徐瀾瞧不下去,把葉濛拉開,趕出廚房,一點兒不客氣地:“行了行了,你別跟這添了,你快把我搟的餃子皮給折騰沒了,除夕飯都快吃不上了,別說看春晚了。我今晚要是因為你錯過沈騰的小品,我弄死你我。”
“您還知道沈騰。”葉濛訝異地都合不攏。
徐瀾翻一白眼,手上流利地刷刷刷包好了三個餃子,“你懂個屁,沈騰同志最近是我跟花的墻頭。”
葉濛科打諢道:“那斗膽問一句,您倆的本命是誰啊?”
大姑在一旁笑著,“你老公啊。”
可以嘛,李靳嶼,師殺手啊。
最后在師殺手的幫助下,餃子包得賊快。三鍋餃子全下好了,徐瀾:“靳嶼會包餃子啊?”
鈄花點點頭,“什麼都會點,前幾年為了照顧我,很多東西都是現學的。”
徐瀾攪著鍋里的餃子,慢慢說:“濛濛就怎麼都學不會,這孩子在廚藝方面就是缺筋。”
“靳嶼會就行了,不死的以后。”花說。
倆老太太對視一眼,笑笑,徐瀾忍不住說道:“花你看看,現在的生活多好。”
除夕那夜,李靳嶼收了很多紅包。
葉濛羨慕不已。
年后,兩人回了老房子住了幾天,那幾天李靳嶼冒還沒好,所以無論葉濛怎麼暗示,李靳嶼都不肯,趴在床上煩得不行,他習慣趴著睡,索整張臉都埋在枕頭里,一把撈過被子罩住整個腦袋,長嘆一口氣,聲音悶悶地從被子里傳出來,可能剛吃完冒藥,他困得眼皮都睜不開,聲音也是充滿睡意的困倦,“不要。我困了,求放過。”
老房子的燈昏昏暗,隔壁墻角還是悉的鍋碗瓢盆的細碎聲,墻頭的梅花,開得眼里,好像人的脂,充滿調氣息。葉濛側躺著,人魚姿勢,一手撐在腦袋上,一手了下他蓬松的頭發:“不行啊你,李靳嶼。”
李靳嶼悶悶地不說話,半晌,從被子里出手,對豎了豎中指。
葉濛笑得不行,突然被他這副無可奈何又只能屈服于的樣子,給可到,于是鉆進被子里,結果李靳嶼已經睡著了。
葉濛在他上親了下。
今年是我們過得第一個新年,雖然你媽媽沒了,我把我給你了,我大姑二姑小姑爺爺都給你了。我也給你,你還要月亮麼,我也可以給你去摘。反正就是,李靳嶼,新年快樂,年年快樂。
“李靳嶼。”
“嗯。”他應得很快,迷迷糊糊很惺忪的那種。
“沒睡?”
“睡了。”
“那怎麼聽見的。”
“說句麻的,”他眼睛閉著,腦袋搭在枕頭上,一副懶洋洋地口氣:“我上每神經都是你的,你只要我,它們就會提醒我。”
“李靳嶼,我你。”葉濛一眨不眨地看著他突然說。
窗外的梅花似乎跟著他的靈魂,輕輕了下。
李靳嶼愣了一會兒,然后翻過,仰面躺著,側頭看著,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:“再說一遍,這邊這只耳朵還沒聽過。”
“……你兩只耳朵分開工作嗎?”
“我一視同仁的,怕它以后罷工。”
“……”
葉濛這次故意湊過去,在他耳朵上咬了一下,“李靳嶼,我有多你,這個世界就有多你。”
“……姐姐,我又行了。/弟弟嗎?”
“……”
——
那年云層高飛,山花格外爛漫,東一簇,西一簇,開遍世界的角落,那年春天的風也格外溫,海浪輕輕拍打著礁石,所有一切都朝氣蓬。
時間其實不會停止,故事仍在繼續。
我們無需為過去的自己道歉,只要過好未來的每一天,就是對過去的自己最大的誠意。
他們至死都浪漫,至死也是年。
至死都要為彼此的月亮。
那是一種連菩薩都無可奈何、明目張膽的偏。
(網絡版番外完。)
- 完結497 章

娇妻在下:总裁大人请克制
一夜宿醉纏綿,路小優卻發現睡錯了人!君夜寒,清河市金錢與權力的象征,更是眾人眼中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!傳聞他不近女色,傳聞他是名副其實的禁欲男神。可是誰能告訴她,這個夜夜求歡,不知節制的是哪位大神。“君少,我……我想,這是個誤會,您要是不解氣,我可以補償……”路小優抓緊小被子縮在床角瑟瑟發抖。“補償?你難道說的不是肉償?”君夜寒挑挑眉,渾身都是不容抗拒的氣息。“我……”路小優差點摔下床,扶著酸痛的腰欲哭無淚。
8 96130 - 完結203 章

帝王攻略
出身皇家,楚淵每一步棋都走得心驚,生怕會一著不慎,落得滿盤皆輸。 十八歲登基,不出半年云南便鬧起內亂,朝中一干老臣心思雖不盡相同,卻都在等著看新帝要如何收場。豈料這頭還沒來得及出響動,千里之外,西南王段白月早已親自率部大殺四方,不出半年便平了亂。 宮內月影稀疏,楚淵親手落下火漆印,將密函八百里加急送往云南——這次又想要朕用何交換? 筆鋒力透紙背,幾乎能看出在寫下這行字時,年輕的帝王是如何憤怒。 段白月慢條斯理攤開紙,只端端正正回了一個字。 你。
8 1940 - 完結50 章

如果星星會說話
“周笑棠小姐,23歲,名校畢業。”年輕的西裝男扶了扶眼鏡,對比了眼前的人和照片上,確認無誤差後又繼續道:“體檢合格,可以簽合同。”
8 10139 - 完結396 章

王爺你家萌妃太囂張了
一朝穿越,她被嫁給曾經權傾天下、俊美無雙,如今昏迷不醒的九千歲沖喜,只盼著他早早歸西,好分家產。 成親后,她每晚對他吹枕邊風:「夫君,與其這樣半死不活,不如早早歸天,下輩子還能做個完整的男人」 誰知有一天,他醒了,她發現他竟然是個假宦官! 最要命的是,她在他「昏迷」 時的所作所為,他都一清二楚,只等著秋後算賬! 「王妃這麼想分家產,不如跟本王多生幾個孩子,如何?」
8.46 53211 - 完結304 章

安息日
脫下厚重而華麗的王冠與禮服,他便與他相逢于樂園了。一句話簡介:阿貴與小梅的鄉村愛情故事——器人阿貴與小梅的異界鄉村愛情故事超可愛的封面
8 335 - 完結68 章
異神錄
“128號,厲陽到你了,別讓劉醫生等急了。”一個穿著白色大褂的中年護士,和藹得對著正在排隊的少年道。
8 135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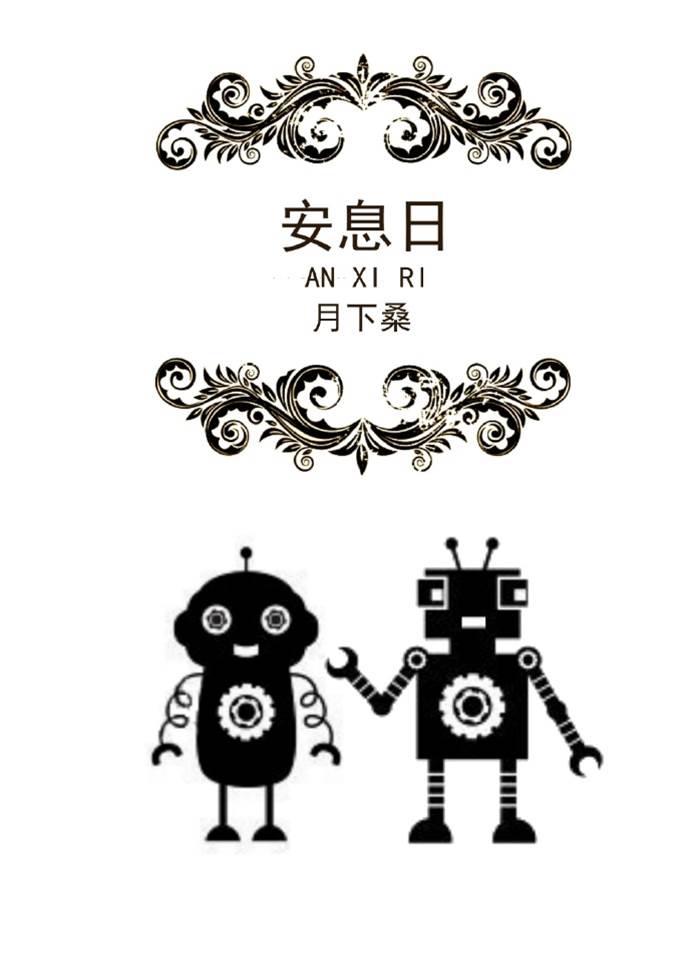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

 男生
男生 女生
女生
